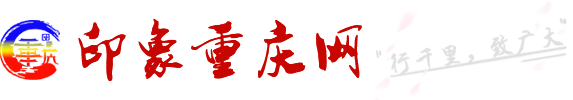老家小西门,是我童年快乐地
发布时间:
2020-12-01
来源:
印象重庆网
作者:
黎强

小时候,我家住江津老县城小西门挨河边的地段。关于小西门的来历,是街坊邻居中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辈子们讲给我听的,大意就是:在明末奢崇明发动叛乱,最后攻破了得胜门,所幸秦良玉率兵前来救城逆转了局势。津城百姓在得胜门举香跪送这位勇猛善战的女将。崇祯十七年,张献忠率兵也是从得胜门处破城。于是,江津有民谣曰:“易守南安门,易破得胜门”。到乾隆时期,因“得胜门不得胜”的原因,遂改名为西城门,原来的西镇门则改名为来庆门。得胜门改名后,在此处至三倒拐处修建了西顺城街,来庆门又被改名为大西门,西城门遂改名为小西门。当然,在我小时候,在小西门我是从未看见过“门”的,倒是看见了长江、纤夫、舟船帆影以及沙滩、鹅卵石,还在老街上看见了黄果树、老院宅、石梯坎……
老槽坊的酒,爸爸夸我长大了
我居住的河坝街不长,不足八百米,满街铺的是青石板,岁月洗礼之后,有的石板已经坑坑洼洼了。在我的记忆中,老街弯七拐八,邻挨邻户挨户大约住了一、二十户人家。从三倒拐至得胜街而下,过一条“雨天一滩泥,晴天一层灰”的环城公路之后,下一坡大约二十七八步的石梯坎,迎面扑来的就是一股酒香——这是在当时县城里难得一见的老槽坊飘出来的。小时候,这老槽坊就像童年的游乐场,老街上、院宅里的小伙伴最爱在夏季集中在这里玩耍,因远离长江玩水的危险,每家大人也较为放心的让娃儿们在槽坊玩。

我家仨兄弟也不例外,常常与小伙伴们在这里玩“躲猫猫”、“抓特务”的游戏,童趣盎然。老槽坊里一个紧挨着一个的发酵池,上等高粱与酒曲发酵之后形成的特殊香味,就是从这发酵池出来的。几十年后,那酒香滋味儿我都记忆犹新。其实去老槽坊玩,还有一个吸引我的原因,就是可以看酿酒师傅蒸煮高粱,一边蒸煮高粱,一边用一个旧瘪的搪瓷盅喝酒。我至今还记得一个络腮胡伯伯,那酒盅是不离手不离口的,按照他的说法——是要品鉴每个酵池酿的酒品质到位没有——以至于我看见他老是醉醺醺的,最怕他那红得发亮的酒糟鼻子。

某天,络腮胡伯伯一改平常严肃的样子,让我挨着他一起坐在蒸煮高粱的大炉膛灶前,给我似醉非醉地摆些我听不懂的龙门阵,还从一匹着实的围腰荷包里抓了一小把砂胡豆给我,怂恿我喝了几口才酿出来的原浆酒。当时,我还觉得甜咪咪的,后来就昏昏沉沉什么也不知道了。待我醒来,已是第二天早晨,我父亲坐在我床边,一句没骂我,还略带自豪感地自言自语到,嘿,这下好了,以后有人给我打酒喝啦!喝酒这事儿,后继有人啦!

老街坊的亲切,我还想回到从前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过得不容易,但邻里之间的客套、客气、关心、关怀,真是想起来就很温暖。
从老槽坊往下去,就到了街中地段,也是家长里短最集中的地方。跑船在外的钟爷家长年只有刘三婆一人独守,靠编蔑巴扇维持生计。李姑婆家子女较多,但左邻右舍的娃儿都喜欢往李姑婆家跑,或是因为隔三差五会得到李姑婆从石灰坛里拿出的五香黄豆或砂炒胡豆一饱口福的缘故吧。
只要到了吃饭时间,张家的娃儿可以端着饭碗,跑到隔壁李家桌上去夹菜。平常时间,随便到哪家哪户去借三勺醋、两勺酱油,不会吃“闭门羹”,更不遭“白眼”、“笑话”。借的人嘴上直说着借了还哈,被借的那家亮开喉咙忙不迭地说,挨邻隔近的,还啥还哟,不够来拿就是。哪怕借的人和被借的人,这俩昨天还为鸡毛蒜皮的事情斗气吵嘴,一见邻居进门讨借,也是一副笑脸儿,还顺口说,昨天的事儿哈,我对不住你哟,过了就算了,改天我推点嫩豆花儿,要来坐哈。

每到腊月小年前几天,在河坝街较有声望的我父亲,就会挨家挨户周知大家,每家自己做一个两个拿手菜,在腊八那天中午聚餐。到了腊八那天,老街上摆了好几桌,都是街坊邻居做的家常菜。邻里之间围坐在一起,你敬我,我请你,好不热闹。除了飘香的好酒好菜,每个人心中都是满满的幸福。有一年,平时很招摇惹事的小年轻马儿,端着酒碗来到我父亲面前,粗声粗气地给我父亲赔礼道歉,说,以后再不会去偷造船厂的船钉呀下脚料呀,要学文化,要去当兵。后来,马儿果然去参军了,还参加了中越自卫反击战,立了三等功。

老家的黄桷树没了,它的威仪还在我心中
老街一隅,有一棵不知道年岁的黄桷树,树冠蓬勃,树荫广袤,既像街坊邻居的共同财产似的,大家非常爱护、也很敬重这棵黄桷树;又像是街坊邻居约定俗成的活动场所,打毛衣的、纳鞋底的、下象棋的、拉家常的,都爱聚集在树下。甚至那些走街串巷卖麻糖的、卖豆瓣的、卖白糕的、卖芝麻杆的,包括补锅的、补席子的,也大多在黄桷树下歇脚或摆摊儿。
黄桷树还是小西门河坝街的标志物、形象大使,或办事,或走亲访友,只要你说找不到,给你指路的人不会给你指什么具体的地方,只给你说到小西门梯坎下那棵大黄桷树,再哪里到哪里,包准错不了。

我们这些娃儿,更是喜欢在黄桷树下“赢烟盒”、“拍豆腐干”、“划甘蔗”等等童年游戏。但娃儿们也最怕夏天晚上下偏东雨,哪怕睡在自己的家里,那电闪雷鸣的阵势,好像是从黄桷树发出的,雷声直落在自己头上、枕头上似的,甚是吓人,只好躲在被窝里不敢出声。大人们也趁机教育娃儿,平常不要说谎话哈,说了谎话,雷公公一冒火,就要找上门来哈!每每这时,黄桷树的威仪才深深烙印在我们这些娃儿心中。
只可惜,那棵陪伴了我童年时光的黄桷树,随着城市开发的进程,消失于小西门河坝街了。而我的内心,一直怀念着它的蓬勃、它的硕大、它的葱郁……
童年,得胜,西门,槽坊,娃儿,就是,一个,街坊邻居,高粱,河坝
上一页
上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