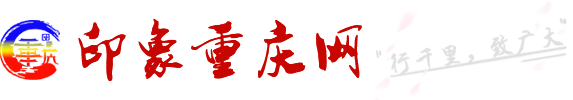那年,我的高考……
发布时间:
2020-11-13
来源:
印象重庆网
作者:
黎强

我是在江津县城工业系统的子弟校工交中学读的高中,那时,只有高二年级。高二年级一毕业,就面临高考的检阅。
临近高考前的一学期,几乎是在死记硬背、文山题海中度过的。不像现在的孩子们,要什么有什么,做不来的题,电脑上、手机上、平板上搜搜就出来了。那时的高考,是需要预考的。我记得全班(包括插班生、复读生)6、70个同学,预考后就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周在赋(总后3539厂工作,江津籍知名画家),每天上课都在邓彬兰老师或刘仁和老师的办公室里进行,因为只有我们俩个准考生,开一间教室没有必要。那时,真让同学们羡慕。我的父母亲也很高兴。

高考前一阵子,左耳是父亲母亲“好好复习,闪不得劲哟”的唠叨,右耳是亲戚街坊“努把力,过了这关就好了”的絮语,整个人完全是晃兮忽兮的,想真正放松下来,其实很不容易,压力之多之大,不比现在的孩子好到哪儿去。
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住在县城河坝街,挨家挨户都晓得我读书得行,都把我当成自己孩子的学习榜样,说自己娃儿,你看别个吃没吃啥,穿没穿啥,读书好凶哟。邻居李二娘还专门给我送来十个鸡蛋,说让我母亲给我补补,好金榜题名。王伯伯喜欢在河边搬罾捕鱼,每有好的鱼,就给我送来,让我母亲熬汤给我喝……。高考头一晚,父亲破例没有醉醺醺的回来,拉了一根长板凳,父子俩坐在一起,从破旧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卤兔脑壳,说,这个给你,明天好好考试。少顷,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在说,你爷爷大字认不得,我也没有啥文化,你妈妈更不消说,黎家没有出过大学生,明天就看你的啦。说完,才自己在碗柜里摸出酒瓶子,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独饮,没有再说一句话了……

第二天,我很早就被母亲叫醒,看样子父亲也很早起来了。我考试需要的东西,都一一给我放在饭桌上了。母亲显得很轻松愉快,从灶房里端来一碗温度刚好的荷包蛋,白白生生的好大两个,还对我说,趁热吃,一根筷子挑两个鸡蛋,肯定考100分。那时,不是太懂得大人的心情,吃得快极了,滋溜一下抹抹嘴角儿,拿着考试必备的东西,走了。老县城的路街,七弯八拐的,要走到考场时,无意间回头,只见父亲掉我不远不近的。父亲看见我发现了他,迟疑了一下,折进旁边的另一条巷子去了。
高考之后,盼的就是分数、成绩,父亲母亲已经数十次问过我的自我感觉,你到底有把握没得哟?你到底把题做完做对没有哟?等等之类让我不敢肯定的问题。临近发通知那几天,我上午、下午,哪里都不去,就端一张小板凳坐在街口那棵黄角树下,听邮递员自行车的铃声。听见铃声一响,心里既高兴又紧张,那几天的心,真是七上八下的。九月中下旬的某天,我终于等来了邮递员喊我名字的那一刻,是考试憧憬单:语文91,数学38,历史79,地理71.5,英语32,我一看,就知道我的大学梦破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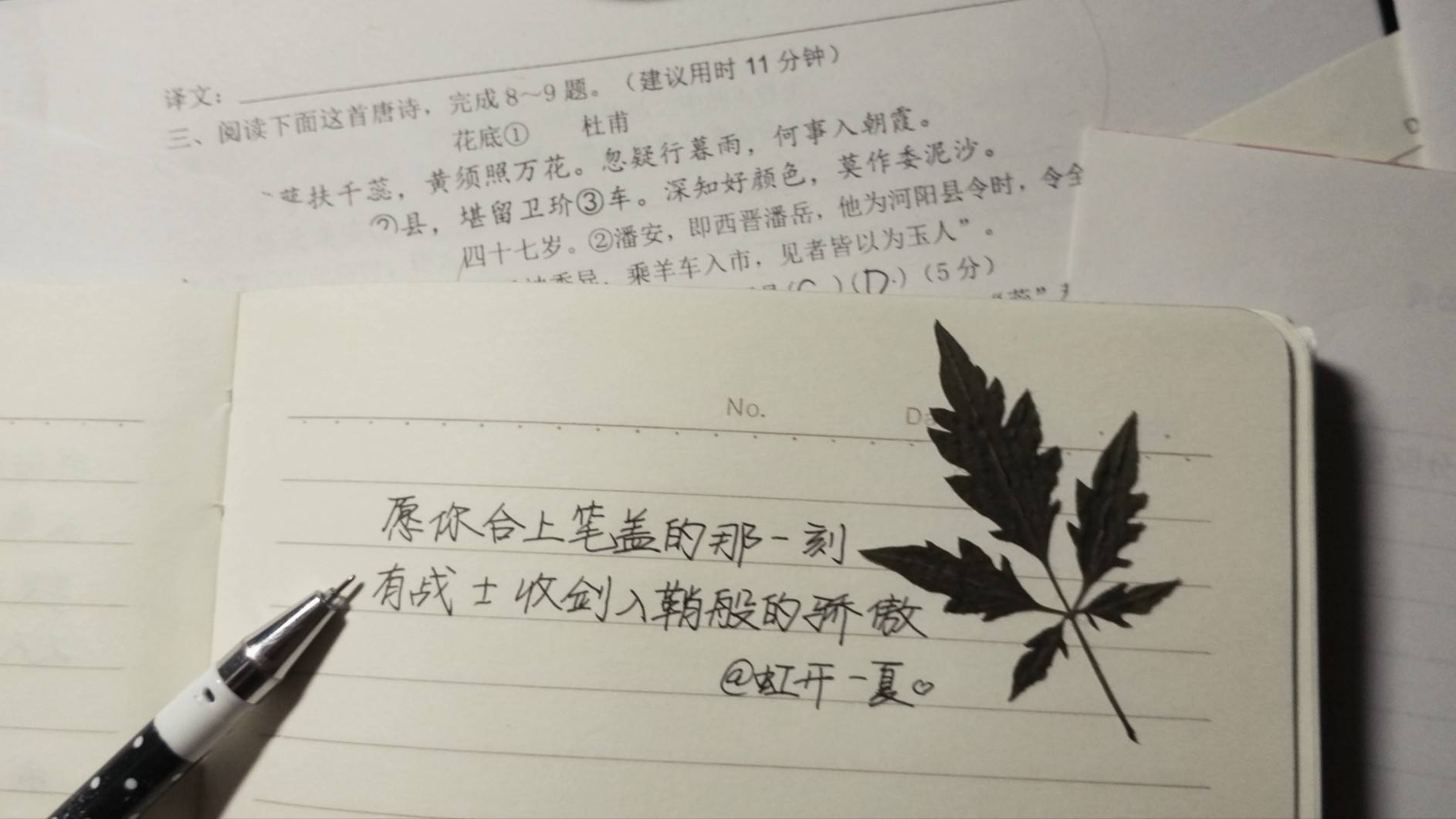
流着极度伤心的泪,我转身回家里,把成绩单递给母亲,母亲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说,晓得下学期复读要好多钱哟,空了我去问问呢——母亲想宽我的心——但我知道家里实在不富裕,哪里有宽裕的钱让我复读呢?!——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亏欠父亲母亲……
第二天,我向母亲要了10元钱,去了四面山深处,我的哥哥在那里的。我去往贵州背炭、去给刚刚改伐的船板打印、去原始森林看伐木工采伐原木……,从此没有在父母亲面前念过一句想读书——其实我内心非常渴望读书——以致于到现在,我都把自己的每一次自学,才当作我对高考失利的惩罚,非常用心。毫不夸张地说,到今天为止,我的自学,早已补偿了我跨入大学校门所学到知识的总和。
这就是我的唯一一次高考,也是我最后一次高考。所以,至今有人问起我的学历,我都会告诉他们,我的学历的高中二年级。那次高考,虽然我没有如愿以偿跨入大学的校门,但高考的失利,却给我源源不断的学习动力,一直旺盛,从未枯竭……
那年,母亲,高考,没有,父亲,自己,给我,考试,那时,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