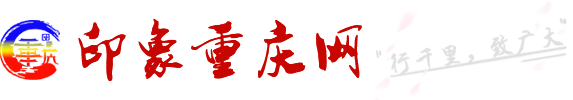海棠溪梦幻曲
发布时间:
2020-01-19
来源:
印象重庆网
作者:
贺 岩

(图片来自于网络)
一
提起海棠溪,一首六十年前的童谣在耳畔响起:
一二三,三二一,解放台湾多安逸。
毛主席,坐飞机;蒋介石,坐撮箕。
一坐坐到海棠溪。
什么意思?无忌的童言,深究不来。倒是六十年前的海棠溪还有些说头。
重庆的主城区被长江嘉陵江分割成三大块。交通往来,必须坐船。南岸就有四个渡口与渝中半岛的四道城门遥相呼应,对接连通:弹子石对朝天门,玄坛庙对东水门,龙门浩对望龙门,海棠溪对储奇门。
六十年前的海棠溪,大致包括盐店湾、丁家嘴、敦厚段、正街、烟雨路、烟雨坡、罗家坝、民生码头等地段。
有渡口就得有渡船。早先,海棠溪的渡口是设在与长江中的珊瑚坝相望的地方,有几株高大的黄葛树,故名黄葛渡。“黄葛晚渡”列为古巴渝十二景之一。“明月清风,渔火泛舟。天水一色,景美人和。”很有些诗意呢。
黄葛渡是一个义渡,来往过客无须交钱。乘船不要钱当然好,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人寿保险。长江水急浪高,一只小木船载几十个人在急奔的江水中颠来簸去,出事是常事,不出事才叫怪事。好在社会在进步,清朝末年,铁甲机动船闯进川江,凡载人都改用了机器船。人命关天,算来算去还是命值钱些,义渡被淘汰出局。
因黄葛渡口水位较低,不适合吃水较深的机动船停靠,于是将渡口迁到了海棠溪。
“赶船”一词在重庆方言中,不但有通用的“乘船”含义,还有追赶的意思,可以称得上是重庆的一道特殊风景线。
六十多年前起,每天清晨,随着“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某某有线广播站,现在开始第一次播音”的声音响起,沿河街的脚步声由少变多、由缓变急,好似追人抓丁。朦胧晨雾中,急着过江上班的人在渡口排着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轮渡订了班次、时间,很准时,正负一般不超过30秒。牢记每班轮渡的开船时间,是重庆人的生活基本功之一。
同在一个城市,来去还要坐船,已经算是稀奇了;汽车也要坐船,更是稀奇中的稀奇。海棠溪不但有人渡码头,还有车渡码头,南来北往的车辆进出重庆城,海棠溪车渡是必经之处,军事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解放重庆时,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就是从海棠溪渡江进入重庆城的。但是没有激战,甚至都没有听见枪声。
同是过一条江,车渡的船就牛逼多了,动力、吨位比人渡的船大,速度更快,人渡晚上要收班,车渡每天24小时换班不停船。船工身穿救生衣,挥小旗吹口哨,指挥车辆上船下船,样子帅呆。晚上人渡一收班,车渡就成了唯一的渡江工具,有急事需过江者就只能打车渡的主意了。
如果恰好那天天气明亮,候渡的车辆不多,工作随心顺手,车辆快上满时,戴着红袖笼的师傅大手一招:“一个个来,快点上,注意安全!”如果天气不好或船工脸色不好,想搭便船的人最好离船越远越好,除非你是正儿八经的国家干部,拿出工作证压得住台。
海棠溪水流较缓,上游金沙江水带来的泥沙受到嘉陵江水的拦截,沉积下来,在海棠溪形成河滩。河滩面积很大,泥沙中混埋着大量鹅卵石,走在上面要十分小心,千万不要踩到“地雷”。重庆的骨科医生已经够忙的了,不要再给他们添累。
旅客下船,先走过几十米长的跳板,然后是更长的河滩,再踏上海棠溪正街的石梯,紧张的心才松弛下来。
二
海棠溪正街原本是连接敦厚段,与黄葛古道相接,直通贵州,修海弹公路时又被截去一节,大概还剩下千五百米长短,其规格布局与其他码头大致相同。正街路面用石板拼镶,一坡石阶接着一坡石阶,街两边多是楼下门面楼上住家的小楼。街道虽然不长,但如麻雀五脏俱全,煤场、米店、菜市场、卫生所、小学校,样样不缺,而且还多了一家别处少见的棺材铺,生活设施完善,构成一个和谐的生活圈。
不知是因为生意不好做或是性格如此,棺材铺老板的脸色就和他的棺材一个颜色,害得行人经过他店门时都不自觉地加快脚步。直到四公里火葬场建成,棺材铺才彻底关门,那张脸也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海弹公路未开通之前,去弹子石方向就得从海棠溪正街左拐走河街。河街有一段吊脚楼,其余多是半边街,沿长江一边没有房屋,靠山坡一边时不时可见几间简陋的平房,多是售卖小面、凉茶、香烟、水果糖等的小摊贩。房主人在门前摆几只小凳,供来往客商歇脚休息,顺便成交一点小买卖,与人方便兼养家糊口。
重庆的夏天热得令人恐怖。河街长三四公里,顶着火红的烈日一路步行,那滋味够得品尝。这时,如果能藏身阴凉处,有一碗冰粉或凉虾,哪怕一杯老荫茶倒进冒烟的喉咙里,效果一定胜过玉液琼浆。
越往山坡上走房屋越多,主要是厂房与仓库。鸦片战争后,重庆被迫开埠,各国行商坐贾蜂拥而来,开公司,办工厂,渝中半岛很快被洋人瓜分殆尽。清政府担心激起民愤,发文禁止在渝中半岛开办大工厂。于是,与渝中隔江相望的海棠溪至弹子石沿江一带成了抢手货,仅海棠溪一片就有火柴厂、医院、电池厂、油漆厂、木材加工厂、制药厂、轮胎厂、库房、私人别墅若干。如果不是因隔江交通不便,运输困难,限制了南岸的发展,重庆可能早就像武汉那样三足鼎立,而非现在的渝中一家坐大。
千百年来,南岸没有一条可以称之为公路的东西。直到抗战时期,陪都重庆成为世界法西斯阵线太平洋战区总部所在地,为了消除日寇轰炸对南山使馆区的威胁,加快重庆的军工生产,南岸修筑了第一条公路,从大兴场经汪山、蒋山、黄山(三山现统称南山)沿真武山脉,在四公里处与川黔公路相接,通向贵州云南,亦经海棠溪渡口进入重庆市中心。海棠溪就成了去云贵的起点,零公里地标,名副其实的咽喉之地。
三
从海棠溪正街往右,经过一段百米左右的石板路,就到了海棠桥。海棠桥原名“通济桥”(据说这三个字是刻在桥拱阴面上的,须涨洪水时仰泳进拱才看得见),清同治六年建成。海棠桥是一座单孔石拱桥,两边配有石栏杆,桥长约八十米,高十米左右,宽可以并排行驶两辆马车。
想想看,在那淤泥堆积、垃圾成堆的溪水与江水汇集处,空旷荒芜的河滩上横跨着这样一座规模超常、造型古朴、气势庄重的石拱桥,能不惹眼招目吗?
桥头曾经长着一株高大笔直的古树,通身墨黑,连流出的树汁,时间长了也变成黑色。方圆几十里再没有一棵与它同种的树。谁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树龄几何?每天来拜访它的乌鸦成群结队,密密麻麻地站满树枝,与古树黑为一体,当地人就叫它“乌鸦树”。乌鸦在汉族被认为不祥,而许多少数民族却视为神鸟,视为祖先,谁也不敢打它们的主意。
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不知是谁得罪了谁,迁怒于乌鸦树,看见乌鸦树就气不顺、心不安,派人砍了乌鸦树。几个人用了一天的时间,断了两根锯条,钝了三把斧头,才把树放倒,巨大的树干还砸断了三条石栏杆。树桩流黑汁十余日,成群的乌鸦围着树桩啼叫乱飞,有的还撞树而亡。民众感动,将树干整体雕刻成龙身,再配上龙头龙尾,组成一艘龙舟,俗称“乌牙儿”。在后来多次龙舟竞赛中,乌牙儿乘风破浪,一往无前,为海棠溪挣得不少荣誉,自己也蜚声山城。
文革开始,乌牙儿也被归于“四旧”,准备碎尸万段。幸有好心人发善心,把它藏起来,堆放在河边一间工棚里。时过境迁,人们忙着奔小康,把它给忘了。从此再也没有听说过与它有关的消息了。
哦,差点忘了,就在这古桥古树的旁边,诞生了闻名遐迩的天下第一味----“桥头火锅”。这石桥、古树、乌鸦与火锅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例如,说火锅的底料中有乌鸦的什么什么之类,空了再慢慢吹。
枯水季节,海棠溪就是一条流水小沟,徒步就可以跨过去,没什么可看的。涨水时期就不同了,其场面的热闹,令人联想起钱塘江观潮。
洪峰下来了!原本宁静平滑的水面隆了起来,发出刺耳的尖啸,鱼儿惊恐地跃出水面。带着巨大能量的洪水被上游狭窄河道困得暴躁不安,看见前面的宽阔河滩,欣喜若狂,万马奔腾般扑了上去。一排浪头滚过,一块河滩沉入水中;又一排浪头压过去,又一块河滩沉入水中,转瞬间,河滩全部消失。余兴未尽的洪水,趁势扑向海棠桥,把它一寸一寸地往水里按。
洪水接近桥拱了,还在石桥看热闹的赶快爬上岸坡,四周的嘈杂声安静下来。拱桥的特点是不怕压,就怕抬。拱上面怎么加重都没关系,下面很小的向上力量就可使拱崩桥塌。所以,每次洪水袭桥,人们都有点提心吊胆。洪水进桥洞了,浪头拍打着拱石“砰砰”作响。洪水一浪接一浪地冲进拱洞,发出气锤般的撞击声,石桥微微颤抖着。最危险的时候到了,已经卷进拱洞的洪水,在后面更多洪水的挤压下,将储存的力量释放出来,形成波浪,凶猛地撞向拱洞,石桥轻微地晃动起来。转瞬之间,洪水封洞,石桥成了“海上孤舟”,但已经安然无恙!
四
那块有十几个足球场大的河滩,看似荒凉寂寞,内涵却很丰富。
这里是天然的儿童乐园。孩子们可以在上面尽力地奔跑,恣意地翻滚,放肆地对着上下行的客船狂呼乱叫。这里是放风筝的最佳地方,高天空阔无碍,而且时时有风。这里好玩的东西多得很:打水漂,看谁的个数多;掷鹅卵石,看谁扔得最远;舀干水坑,里面竟有两条小鱼;搬开石头,一只螃蟹在张牙舞爪……
这里还是巨大的天然仓库。河滩上的物资丰富得超乎想象,特别是在洪水刚退尽时,这里比赶场还热闹。有人刚捡到一张塑料布,有人拾起一个罐头壳;这边高喊“我捡到一根铁丝。”那边马上宣告“我找到一块玻璃!”还有更惊喜的声音飞过来:“啊,铅笔刀!”
当然,这众多的财富都无法与它蕴藏的黄金相比。每年洪水退去后,就会有几只不知从哪里飘来的小木船,停靠在河滩边一个被叫做鸡翅膀的地方。船中间有棚,隐约看见有做饭的用具。仔细观察,每只船就是一家人,船就是家。他们在河滩上支起一个约70度的脚架,脚架上搭一块搓衣板似的木板,木板上罩一张钢丝筛,支架顶部是一个长方形的漏斗。他们三人一组,一人把砂石铲进漏斗,一人用小桶舀江水倒进漏斗,另一人负责把过筛后的砂石铲去。一堆砂石冲洗完了,从支架的最下方抽出一块沾满沙粒的小木条,用布盖着,小心翼翼地回到船舱,放下门帘,外面的人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有好奇者打听,回答说:“掏金的。莫看穿得烂糟糟的,有钱得很!”
河滩的另一功绩,是为众多无处可去的痴男怨女提供了安静又相对安全的约会地点。那静静的江水不知带走了多少摧肝断肠的眼泪,那坚硬的鹅卵石下不知埋藏了多少酸甜苦辣的故事。
五
地处烟雨路的长途汽车站,是海棠溪的“不夜城”,每天24小时都在发车接车,南来北往的旅客经常把候车室挤得满满的,它周围不是饭馆就是旅馆。停车场停放着十来部客车,车顶上背着个大气包,把原本就矮小的车厢压得喘不过气来。汽车开动,汽包就前后左右地摇呀摇,真担心它从车顶上摔下来。
每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车站出口出就会出现一个老者,中等身材,着吊带西裤,浅色衬衣,系红色领带,杵着拐杖,笔直的站在那里。他仔细地观察下车的每一个旅客,直到人流走尽,他才转身离去。每个询问他的人,得到的回答就两个字:“等人。”

(图片来自于网络)
按理说,“海棠烟雨”是古巴渝十二景之一,应该留有一些诗情画意的东西,如“海棠依依付流水,烟雨蒙蒙送暗香。”可是眼前,海棠不再,金桂难觅。就是一个大码头,常往常来的就两种人:搬运工,旅客。主要营业:饭馆(其中有正宗回族饭馆,门前挂着“清真教门,外菜莫入”标志)、旅店、茶馆;主要文化生活:下酒店,坐茶馆,打长牌(川牌)、扑克牌。那时麻将属“四旧”,没人敢碰。
晚上,到茶馆听评书,要算最高级的文化享受了。说书人独坐台上,布褂长衫,手执折扇,神情自若,一桌、一椅、一抚尺而已。7点钟一到,醒木“砰”一声响,原本闹哄哄乱糟糟的茶馆顿时鸦雀无声,说书人朗声道白:“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春秋战国秦与汉,唐宋明清民国现。英雄成败悲与欢,请君听我细细谈!”
不得不佩服说书人,没有话筒扩音器,没有剧本没道具,没有导演和帮腔,仅靠一把折扇一块醒木,单打独斗俩钟头,字正腔圆吐莲花,或说或唱或口技,如行云若流水;二胡、笛子、快板、道情、锣鼓,样样得心应手。
最得益的还是孩子们。在那没有电视机、买不起收音机、饥肠响如鼓的年代,他们忍饥挨饿,踮疼了脚尖,伸长了脖子,把我们老祖宗传说下来的那点东西偷听进了耳朵,藏进了肚子里……
哎,海棠溪,这就是留在记忆中的海棠溪。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现在的海棠溪已经面目全非了。码头没有了,渡船没有了,长途站没有了,旅社茶馆没有了,连那长长的河滩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厦林立,华灯炫目,如梦如幻的南滨路、和用水泥条石砌成的防波堤。江水傻呆呆地从石壁匣子里流过,一张生硬脸,完全失去了过去温柔多情的曲线美。
那座喧闹一时的大石桥,如今静静地埋在地下,成为两座金碧辉煌的大厦的奠基石,永不得见天日,但与粉身碎骨比较起来,也算是善终了。
老实说,眼前的海棠溪比记忆中的海棠溪美多了,富多了。可是记忆中的海棠好像是在大脑里扎了根,怎么都甩不掉。故乡啊!打断骨头也连着筋啊!
海棠溪没有了。留下的是传说与故事。这些传说与故事还会流传下去吗?
写于2020年1月16日
【责任编辑:胡笳十八拍】
【作者简介:贺岩,男,号一蓑客,重庆荣昌人。1965年初中毕业,先后在四川省南江、内江两县当知青近八年。1973年回城任小学教师。恢复高考后,1978年考入渝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学任教直至退休。发表多篇文艺作品,出版百万字自传体长篇小说《凡尘天歌》(三部曲),该书中的一章《牛刀小试》获2019年“中国知青作家杯一等奖”,现为中华知青作协副主席】
声明:本栏欢迎各种题材的纪实文学、人物传记、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写实书画;凡投稿必须为作者原创,在报刊杂志公开发表过的稿件请注明出处,文章后附300字以内作者简介,发表时署名听便。投稿后不得再投向在其他微刊(公众平台),20日内未见刊用或者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来稿严禁抄袭、侵权,文责自负,本平台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投稿邮箱: 憨憨:101024125@qq.com
胡笳十八拍 :184000193@qq.com
海棠溪梦幻曲
上一页
上一页